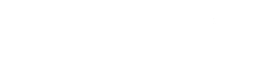第六届H50年会高峰对话|前沿技术对产业的启迪助推
时间:2023-06-02
5月28日,第六届H50年度峰会暨中国医疗医药科技发展论坛在北京顺利举办。来自政府、医疗学术界、产业投资界等相关领导、专家和企业家齐聚一堂,研讨前沿科技、洞察产业发展,指引投资方向。
会上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、百济神州、维泰瑞隆创始人王晓东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、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,H50创始主席、华盖资本创始合伙人、董事长许小林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巅峰对话,围绕医药前沿技术发展、科研的应用及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研讨,洞察未来发展。
以下是《前沿技术对产业的启迪助推》专题讨论的
对话实录,经医药魔方Invest编辑整理:
许小林:前沿技术对产业越来越重要,1902年的今天(5月28日),爱迪生发明了新式的蓄电电池,为什么讲这件事?今天电动汽车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,而一百多年前新型技术对产业的推动是巨大的,所以我们也想探讨生物医学领域的前沿技术的发展。
我想问两位院士第一个问题,关于中国医学前沿技术的现状,或者说政府、资本、学界究竟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它的发展?
王晓东:这是我六年后再一次来到H50的会场,当时我给大家介绍,北生所在做的很多科研有转化的前景。六年后给大家汇报一下,北生所成立了六家公司,其中包括维泰瑞隆。
我在过去这些年的创业中观察到一个问题,大家谈的都是已经知道的技术的发展,比如AI制药,但如果仔细问AI制药的核心是什么?对制药的贡献是什么?大家最后可能意识到——它其实是一个推动,而不是改变行业规则。
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行业的规则,例如从原来成功研发出一款药物需要“10亿美金10年”,缩短到“7亿美金7年”,甚至“5亿美金5年”,这就是对行业巨大的推动。如果科技真正发展起来了,那么从靶点到化合物,将不是需要几年,可能只需要几天的时间,制药过程中的风险可能在早期就能够排除了。
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在这儿讨论的技术,都是已经扎堆的技术了。像我们这种天天在技术堆里打滚的人知道,其实任何技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,都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地方。到了大家都能看到都能评估的阶段,在我看来已经晚了。
我再一次呼吁投资人,不要跟着某些人跑了,而要真正地和在一线的科学家建立有机的联系。比如大家都可以去办一张北生所食堂的饭卡,现在有一些投资人已经这么做了。在事物真正发展起来之前,要有风险意识并且能做出独特的判断。
许小林:谢谢王晓东院士,董院士在治疗的一线,也在清华大学管理研究的一线,您对于这些前沿技术等方面有没有不同的意见?
董家鸿:从当前的前沿科技来看,我作为临床医生比较看重这几个方面——新药的创制,比如AI药物的研发、小分子药、靶向药、核素类药品。在核素的研发方面,基础的核能、核武器军事上应用很好,民生、医疗上还需要更大的发展,最近国内率先引进的钇90玻璃微球临床治疗肝癌的效果非常好,核素药物还有很多应用,这是一个蓝海。
另外就是数字制造,像3D打印。还有传统的高端医疗设备通过数字化升级,提高性能和效率,这涉及到工程的原理和智能制造。
第三我还比较看重数字健康,包括最近特别火的ChatGPT、大模型、机器人等,还有社区的健康医疗,我们和北京市昌平区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合作——天北社区医疗,那里有清华研发的数智健康医疗联合体。基层是我国医疗体系中最匮乏、最薄弱的环节,我们现在培养不出那么多全科医生,所以希望先进技术能够辐射到基层去。
许小林:有时候投资人也好、政府也好,他们的苦恼是如果像两位这样的大专家创业,大家都愿意投,但当前沿技术新的领军人物还没出现,大家应该怎么做?怎么培养科学家做产业转化?搞技术研究的人怎么和做临床研究的人合作?两位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?
董家鸿:我们现在的科研需要强化应用驱动型的研究,现代科学发展到现在有两种基本的研究的模式:一是认知驱动型,主要是科学家的兴趣,着眼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,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,是非功利性的;二是应用驱动型,就是有明确的应用场景的需求,解决实际问题,以研发新颖的实用的产品为目标,有明确的功利性。
我们过去的科研体系其实是有缺陷的,就是只为研究而研究。现在的研究应该要为应用而研究,从开始立项的时候,就紧紧把握两个方向:一是需求牵引,二是产品导向。需求牵引就是针对医疗实践服务中的痛点和难点,研究那些没有被满足的医疗需求,以及没有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。
医疗研究的重点方向应该转向疾病负担最大的领域,比如心脑血管疾病、肿瘤、慢阻肺这一类。那些未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,应该是着力点。另外如果研究最终没有形成产品,那就体现不出它的市场价值,也会很难持续。
许小林:董院士说到我们心里了,因为投资人的钱都是有时间表的,如果没有应用场景,没有明确导向型的研究,我们投进去就不知道何时能退出来。但是科学家做研究可能想的是一定要自由,不能有太强的目的性,不能设立时间表让他交东西。王院士对此是什么样的观点?
王晓东: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,不仅是在座很多人关心的问题,也是整个人类发展很重要的问题。科学界在社会发展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要不要起作用?这个价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?
科学研究要有四个“面向”,这是非常清晰的方向和标准。这个标准没问题,因为现在的科学研究绝大多数的支持是来自于政府。政府的诉求是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,这个没有任何逻辑上的问题,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科学家要有自我兴趣的驱动,好像科学家也要自娱自乐,也要有象牙塔。
其实这包含两个问题,一个是历史问题,如果看现代科学的发展,它来源于科学家自身想要了解未知的驱动,这也是人类自有的一种驱动力。像宇宙的起源,我也关注望远镜,现在可以看到宇宙大爆炸起源1亿年这样的事情了,但它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?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对这种事情感兴趣,这是因为我们有内在的需求,可能不是说物质上可见的需求,但这是我们精神需求的一部分。
其实科学界的形成和对未来世界的探索一脉相承,所以传统科学研究的活动,完全由自己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所驱动的。现在科学发展到21世纪,科技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,如今对科学家的要求与从前的学术传统是有冲突的,比如没有达到四个“面向”的要求,还有科学家团队本身的焦虑。
科学家团队要意识到新时代不一样了,当然要肯定科学家团队自我驱动的价值。在这个过程中,它培养了新一代的科学家以及源源不断的人才队伍,这也是有价值。
那么区别就是,科学家研究的目标应该以现实问题为导向,还是以自娱自乐发表文章为导向?其实发了文章,大家现在都知道谁还会读呢。尤其是AI、ChatGPT来了,现在文章实在太多了,一个领域的每天都有那么多文章,谁读得过来。
在我看来天天什么事不干就读文章,而且读了文章还专门发在微信圈,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精读了。前天我们实验室还讨论一篇文章,关于饥饿感本身不见得要饿,有饥饿感本身就要延寿,不见得是吃饱了撑的问题,吃饱了饿的问题,结果读了一篇文章,它的结论和数据是相反的。
但是现在这种文章都能发在《科学》杂志上,我们也很奇怪。现在文章推送出去都不看数据只看标题就行了吗?这也是科学界面临的问题,在知识爆炸的阶段,我们每个人都要专业化,专业到自己最精的地方还要精。
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能再和传统的科学家一样,能够安贫乐道。这是科学界自己的问题,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,研究肯定会变成自娱自乐,甚至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,连自己的初心恐怕也没有了。
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,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科学界自己也有既得利益,它也是个利益集团,可以用各种形式拿政府的钱,拿投资人的钱,最后也不知道它做没做事。其实我当时去做实业,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看到了这种问题:最后不仅是“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”,而且是“秀才遇到秀才,有理也说不清了”,你跟他说数据,他跟你说情怀,你跟他说情怀,他跟你要数据。
还是要走到经济战场,你的东西好就是好,就像董院士说的那个治肝癌的方法,确实能让病人活得更久,用别的方法病人活得短一些。所以要把目标和成果检验转向第一线,这是科技界的一个刚需。如果科技界不解决现在这个危机,最后和骗子也没区别了。
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那就是现实社会的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解决,但是科学的方法都有内在的规律。上世纪70年代,美国推出了“癌症计划”,它在登月计划完成后,后者用了十几年就实现登月了,但是“癌症计划”推行了几十年,最后研究癌症的人比得癌症的人还多。其实任何一个社会活动,都有可能形成这种利益集团,这个利益集团最后变成了——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。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?
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,举一个典型的例子,有人吃了五个烧饼吃饱了,但是你不能说前四个烧饼都是白吃了,每一步都要有具体的过程。像癌症免疫治疗,它在最开始的时候,科学家并不知道它与癌症治疗有关。
人类意识有它的阶段性和局限性,从这一点上,还是要给科学家研究的自由,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。“西方不亮东方亮”、“无意插柳柳成荫”,这是科学的常态,所以需要花园里该插柳的插柳,该种花的种花。不要说,插柳和花园有什么关系,现在可能看不出来,但它可能是最终解决方案必经的一个路径。
许小林:这已经是一篇非常好的演讲了,虽然王晓东院士已经创立了一个2000亿元市值的公司,但是骨子里还是一个科学家。六年前您来H50的时候,当时流传最经典的一句话是——人不是要思考将来能活多久的问题,而是活那么久干什么的问题。刚刚谈到衰老,因为您是这方面最顶尖的专家了,那么您觉得我们活到120岁还有多久可以实现?
王晓东:在最近的一个论坛上我回答了这个问题,结果讲完以后我就受到了网暴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被网暴,感觉很差。网上一大堆评论都在说,长这么老的人还敢讲抗衰老,一看就是对照组的。
我当时讲的核心内容是这样:如果我们把生命体看成一个生命精密的仪器,所谓衰老的过程,我们是否能够以工程师的眼光,来看这个过程中内在的逻辑,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节点进行干预,从而把衰老的过程延缓甚至阻断。这个过程显然是非常复杂的,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,我们在很多不同动物的遗传筛选表现上,看到了这些节点。
当时维泰瑞隆有一个经典的视频,里面年龄很大的老鼠看起来依旧年轻,并且在很多行为方面也很年轻。其实展示这个的目的是,衰老是可以在科学上理解的。
董家鸿:我同意王院士的观点,衰老是可以干预的,虽然最终不能永生,但是针对衰老机制的研究,最终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,外科医生不希望人是永生的,永生的话,我们医生就失业了。
许小林:外科医生说,药物学家能解决问题,还要我们外科医生做什么。您作为一位顶尖的外科医生,如果药物研发的前沿技术这么发展下去,甚至人都有可能长生不老,那么将来药物会替代手术吗?
董家鸿:首先我作为外科医生,是希望未来外科医生完全失业,人类不再需要外科医生的。因为外科是有创的手段,毕竟不是一种理想的治疗手段,如果一种疾病能够通过药物治疗的话,那还需要手术干什么?所以我虽然是外科医生,我宁愿世间没有外科疾病,将来都是内科医生。
第二,随着社会的发展,现在医疗是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变成健康为中心,加强健康的管理,早期的筛查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疾病。而疾病的早期治疗更多通过药物控制甚至治愈,那么可能也不需要外科手术了,所以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外科医生失业。
许小林:这也是一个来自一线治疗领域大专家的心声,所以您两位都是从人类的福祉出发来讨论的。我们谈一个热点的问题,医保政策是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很关注的,对于这几年医保政策的调整,两位是怎么看待的?
王晓东:其实我来这儿之前,和三叶草生物开会,它的新冠疫苗应该是最完整,并且受到国际流行性大联盟支持最多的。结果现在新冠疫苗一集采,收入可能会受到很大冲击。
许小林:进入不到产业化的的阶段?
王晓东:能进入到产业化,也商业化了,但是采购的价格连买物料都不够,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我想投资人可能更加感同身受,就是这样一个行业,一方面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,因为人民不断提高对健康的要求,那是社会的刚需。但是如果你投的钱最后回不来,后果也很清楚,我们以前也都经历过,就像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那种情况可能会重现。
尤其在现阶段,很多企业活下来都变成了一个问题。其实新药研发的快速发展,也就是过去几年的事,那么这个势头能不能维持下去,能不能走过行业周期里寒冬的时代?一方面我们能否真正走向国际化,另外一方面,我们是否能真正满足刚需,不会受到这种政策因素的影响,比如集采、国谈等?
我们最终恐怕还是要练内功,因为只要能满足刚需,国际化也会容易,包括收购、融资也都会容易。前面一个阶段,大家的投资逻辑更多的是“你有没有一个商业故事”,现在是对我们所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那就是对需求、对科学内涵、市场上的位置的要求,而之后可能会出现非常有竞争力的企业,它们逐渐成长起来,这是大家的期待。
许小林:医保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让大家认识到,必须要投真正的创新,要投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企业和产品。这可能也让投资人、社会各界都理性下来。董院士您有什么补充?
董家鸿:对于临床来讲,我们需要创新药解决临床上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,治疗效果不好的这些疾病。那就是说,医保应该鼓励原创的药物、器械,关键是对它们的使用价值进行科学评价,有了科学评价,并且得到了临床试验的证明,医保需要开绿灯。
另外,资源的投入和现实的需求之间需要平衡,医保的本质是一定的资源投入,来保障全民的基本健康,但有了更有效的药物以后,有助于医保实现这样的目标。